对别的孩子来说,生在一个爸爸是政府官员、妈妈是大学教授的家庭,是多么幸运。但对我却是一种压力,我不但没有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而且还是一名多动症儿童。

两岁半时,别的孩子唐诗宋词已经张口就来,我却连10以内的数都数不清楚。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就打伤了小朋友,还损坏了园里最贵的那架钢琴。之后,我换了好多家幼儿园,可待得最长的也没超过10天。
爸爸不许妈妈再为我找幼儿园,妈妈不同意,她说孩子总要跟外界接触,不可能让他在家待一辈子。于是我又来到了一家幼儿园,那天,我将一泡尿撒在了小朋友的饭碗里。妈妈出差在外,闻讯赶来的爸爸恼怒极了,将我拴在客厅里。我嗓子都喊哑了,手腕被铁链子硌出一道道血痕。我逮住机会,砸了家里的电视,把爸爸书房里的书以及一些重要资料全部烧了,最后连消防队都被惊动了。
爸爸丢尽了脸面,使出最后一招,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一个月后,妈妈回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跟爸爸离婚,第二件便是接我回家。妈妈握着我伤痕累累的手臂,哭得惊天动地。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上了小学,许多老师仍不肯接收我。最后,是妈妈的同学魏老师收下我。我的确做到了在妈妈面前的许诺:不再对同学施以暴力。但学校里各种设施却不在许诺的范围内,它们接二连三地遭了殃。一天,魏老师把我领到一间教室,对我说:“这里都是你弄伤的伤员,你来帮它们治病吧。”
我很乐意做这种“救死扶伤”的事情。我用压岁钱买来了螺丝刀、钳子、电焊、电瓶等等,然后将眼前的零件自由组合,这些破铜烂铁在我手里生动起来。不久,一辆小汽车、一架左右翅膀长短不一的小飞机就诞生了。
我身边渐渐有了同学,我教他们用平时家长根本不让动的工具。我不再用拳头来赢得关注,目光也变得友善、温和起来。
直到小学毕业时,魏老师才告诉我真相。原来,学校里的那间专门收治受伤设施的“病房”是我妈妈租下来的。妈妈通过这种方法为我多余的精力找到一个发泄口,并“无心插柳”地开发了我在机械方面的天赋。
我的小学在快乐中结束了。上了初中,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让我再次成为批评的对象——不按时完成作业、经常损坏实验室的用品,更重要的是,班主任极不喜欢我。班主任在课上从不提问我,她还以我不遵守纪律为由罚我每天放学打扫教室。
妈妈到学校见我一个人在教室扫地、拖地,哭了。从此,她每天下班后便来学校帮我一起打扫卫生,她说:“儿子,无论何时,妈妈都是你的坚强后盾。”
再辜负您一次
初中临近毕业,以我的成绩根本考不上任何高中。我着急起来,跟自己较上了劲儿,甚至拿头往墙上撞。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绝食、静坐。
整整4天,我在屋内,妈妈在屋外。我不吃,她也不吃。第四天,小学班主任魏老师来了,她对我说:“江江,我教过的学生里你不是最优秀的,但你是最与众不同的。你发明的那个电动吸尘黑板擦我至今还在用,老师为你感到骄傲。”魏老师走后,我蹑手蹑脚走出了门,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我站在她身后,说:“妈,对不起,我觉得自己特别丢人。”妈妈转身把我搂在怀里,说:“我儿子为了上进不吃不喝,妈为你自豪。”
半个月后,妈妈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A、去一中,本市最好的高中。B、去职业高中学汽车修理。C、如果都不满意,妈妈尊重你的选择。”我选了B。我说:“妈,我不想读高中了,恐怕要再辜负您一次。”妈妈摸摸我的头:“傻孩子,你太小瞧你妈了,去职高是放大你的长处,而去一中是在经营你的短处。妈好歹也是大学教授,这点儿脑筋还是有的。”
我是笨鸟,你是矮树枝
就这样,我上了职高,学汽车修理。我们住在理工大学的家属院,同院的孩子最差的也是研究生毕业。只有我,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院里的反面教材。
妈妈从不因为有一个“现眼”的儿子对人家绕道而行,相反,如果知道谁家的车出了毛病,她总是让我去帮忙。我修车时她就站在旁边,一脸的满足,仿佛她儿子修的不是汽车,而是航空母舰。
我的人生渐入佳境,还未毕业就被称为“汽车神童”,专治汽车的各种疑难杂症。毕业后,我开了一家汽修店,虽然只给身价百万以上的座驾服务,然而生意非常好——我每天一身油污,但不必为了生计点头哈腰、委曲求全。
有一天,我在一本书中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句谚语:“上帝为每一只笨鸟都准备了一个矮树枝。”是啊,我就是那只笨鸟,但给我送来矮树枝的人,不是上帝,而是我的妈妈。
 扫一扫,订阅母婴精选知识
扫一扫,订阅母婴精选知识
 儿童教育
儿童教育
 春季穿什么衣服好
春季穿什么衣服好  春季如何预防流感
春季如何预防流感  春季养肝方法大全
春季养肝方法大全  春季养生吃什么好
春季养生吃什么好  春季如何养心调神
春季如何养心调神  春季要预防哪些疾病
春季要预防哪些疾病  监测排卵的步骤
监测排卵的步骤  怎样赶走小三?
怎样赶走小三?  男人为什么会出轨
男人为什么会出轨  哪种女人容易出轨
哪种女人容易出轨  如何应对七年之痒
如何应对七年之痒  宫颈癌疫苗怎么打
宫颈癌疫苗怎么打  冻疮的治疗方法
冻疮的治疗方法  毛孔堵塞怎么清理
毛孔堵塞怎么清理  雾霾天怎么护肤
雾霾天怎么护肤  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
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  唇纹怎么去除
唇纹怎么去除  鸡皮肤怎么消除
鸡皮肤怎么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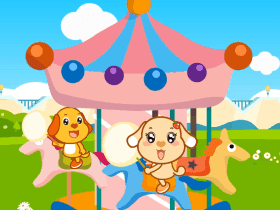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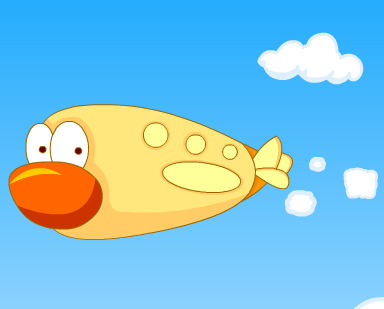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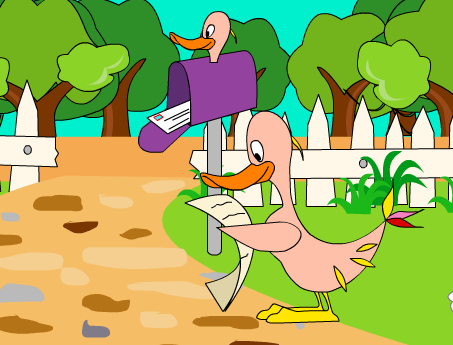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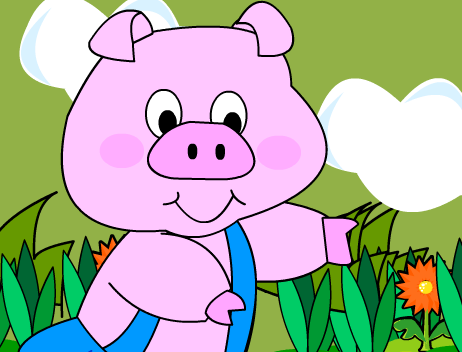


































 犀利辣妈小S的育儿法则
犀利辣妈小S的育儿法则  孩子不愿意分享玩具是“小气”吗
孩子不愿意分享玩具是“小气”吗  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该怎么给孩子选择零食?
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该怎么给孩子选择零食?  那些年骗过我们的外伤处理方法
那些年骗过我们的外伤处理方法  最幸福的事:生个可爱的孩子,养条笨笨的狗
最幸福的事:生个可爱的孩子,养条笨笨的狗  林志颖幸福晒双胞胎 个个大眼萌萌哒
林志颖幸福晒双胞胎 个个大眼萌萌哒  章子怡爱女“醒醒”成长照曝光 圆脸呆萌可爱
章子怡爱女“醒醒”成长照曝光 圆脸呆萌可爱  欧弟爱女一百天了,全家同穿亲子装温馨合影
欧弟爱女一百天了,全家同穿亲子装温馨合影  黄奕携三岁爱女登封面 母女亲子装十分有爱
黄奕携三岁爱女登封面 母女亲子装十分有爱  宠物犬与小主人穿同款服装萌翻网络
宠物犬与小主人穿同款服装萌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