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测她是去进修的吧,像浮萍一样,在这座城市这家医院待了短暂时光,与我有这么几分钟的交集。她只是以她的方式,给了我,温柔与慈悲。
她是湖北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大约是进修医生,胸前并没挂名牌。我只是,听出了她的口音。而我太慌张,忘了告诉她:“我与你,是老乡。”
那时我已经怀孕13周,生命已经在对我嘻皮笑脸,尽情恶作剧。
那天照例排队做产检,照例挂号大厅里人山人海,7点10分抵达,7点35挂上号,11点才轮到。胎心仪上肚,一片阒然,医生把胎心仪转来转去,我紧张得自己的心脏也快停跳了。

挂号室好吵,女人们——全是产妇——的嗓子是真尖,突然不合宜地听见窗外的鸟鸣。而我丰饶的身体,像沉默的大地。
她把胎心仪放下,对我说:“去上个厕所吧。回来再听。”——这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节奏吗?看我一眼,“不用担心的,这有什么可哭的。去个厕所就没事了。”
我其实没有哭泣,那更像是一种本能反应,像被锤子敲中手指,疼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迸出泪。
我慌慌张张下地,恍惚得忘了要整理衣服,差点准备露着大肚皮招摇过市。她喊住我:“衣服。”递过卫生纸来。
我敷衍了事擦几下肚子上的B超液,游魂一样扑向门外。她又叫住我:“你的包——算了给我吧,你快去上。”我慌不择路、双股栗栗地去上厕所。虽然完全不理会大小便与胎心的关系,还是尽责地努力做了,哆哆嗦嗦地回来了。
看到我,她放下正在诊疗的产妇,站起身对人家耐心地说:“我先给这个同志听一下,她刚刚听了一半。”
我已经迫不及待,宽衣解带。
这一次,胎心仪一放上来,结实有力的“马蹄”声便响彻耳畔。我喜极而泣:“谢谢谢谢谢谢!”便失控地开始擦泪。连她都笑了:“又不是我做了什么。”
不,她做了,只是她不知道。去妇产医院一年,听惯医生淡漠的论断,无数次被突来的坏消息吓得眼泪夺眶而出。总是赤身裸体在陌生人之间,如待祭的羔羊,抓不到一只温热的手。她的耐心,她的爽朗,我听来无比稔熟的湖北口音,让她像我的熟人,像朝夕相处过、打过招呼的人,是茫茫沙海里,能一眼认出的地标,可以确定方向。
之前之后都没有见过这位医生,更让我确定她只是去进修的。她像浮萍一样,在这座城市这座医院待了短暂时光,与我有这么几分钟的交集。她一定不记得我了,我替妇产医院的医生们算过,每5分钟一个产妇的话,一天要按100个肚子,一年就是两万个。两万个柔软的恐惧,两万个蓬勃的热望。而她,也可能根本没觉得,她为我做过什么。
顺带插一句:为什么她要我去卫生间呢?后来我才想通,我一直为下一步的B超憋着尿,而太厚的尿液,像穿越不过去的海,挡住了胎心的传播。
多年前, 我在网上听过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歌,叫《不要欺负我们湖北人》,歌中唱道:湖北人是相信爱情、梦想与奇迹的人。想到这位女医生,她夹杂在普通话里的湖北口音,我就想起那首歌。
 扫一扫,订阅母婴精选知识
扫一扫,订阅母婴精选知识
 孕期检查
孕期检查
 春季穿什么衣服好
春季穿什么衣服好  春季如何预防流感
春季如何预防流感  春季养肝方法大全
春季养肝方法大全  春季养生吃什么好
春季养生吃什么好  春季如何养心调神
春季如何养心调神  春季要预防哪些疾病
春季要预防哪些疾病  监测排卵的步骤
监测排卵的步骤  怎样赶走小三?
怎样赶走小三?  男人为什么会出轨
男人为什么会出轨  哪种女人容易出轨
哪种女人容易出轨  如何应对七年之痒
如何应对七年之痒  宫颈癌疫苗怎么打
宫颈癌疫苗怎么打  冻疮的治疗方法
冻疮的治疗方法  毛孔堵塞怎么清理
毛孔堵塞怎么清理  雾霾天怎么护肤
雾霾天怎么护肤  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
眼霜的正确使用方法  唇纹怎么去除
唇纹怎么去除  鸡皮肤怎么消除
鸡皮肤怎么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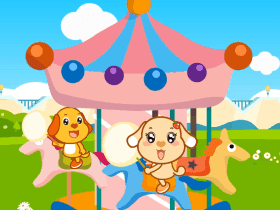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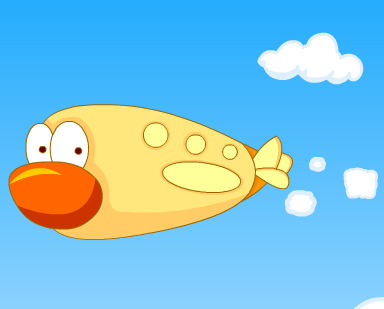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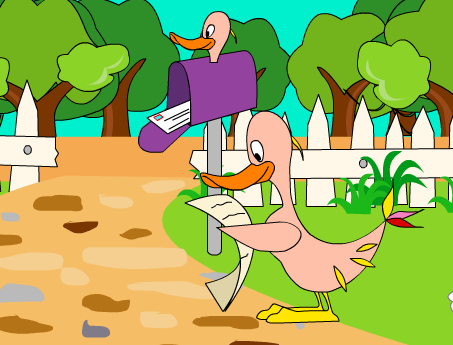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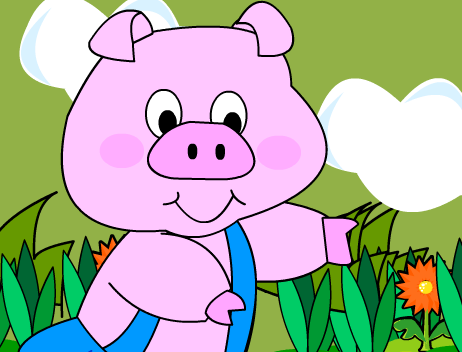


































 犀利辣妈小S的育儿法则
犀利辣妈小S的育儿法则  孩子不愿意分享玩具是“小气”吗
孩子不愿意分享玩具是“小气”吗  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该怎么给孩子选择零食?
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该怎么给孩子选择零食?  那些年骗过我们的外伤处理方法
那些年骗过我们的外伤处理方法  最幸福的事:生个可爱的孩子,养条笨笨的狗
最幸福的事:生个可爱的孩子,养条笨笨的狗  林志颖幸福晒双胞胎 个个大眼萌萌哒
林志颖幸福晒双胞胎 个个大眼萌萌哒  章子怡爱女“醒醒”成长照曝光 圆脸呆萌可爱
章子怡爱女“醒醒”成长照曝光 圆脸呆萌可爱  欧弟爱女一百天了,全家同穿亲子装温馨合影
欧弟爱女一百天了,全家同穿亲子装温馨合影  黄奕携三岁爱女登封面 母女亲子装十分有爱
黄奕携三岁爱女登封面 母女亲子装十分有爱  宠物犬与小主人穿同款服装萌翻网络
宠物犬与小主人穿同款服装萌翻网络 